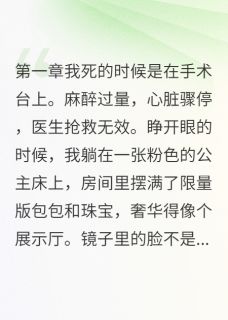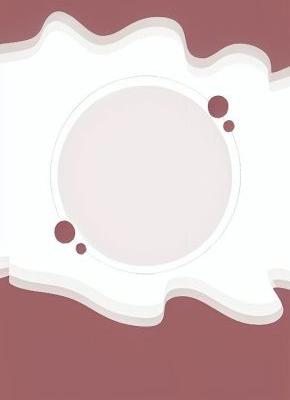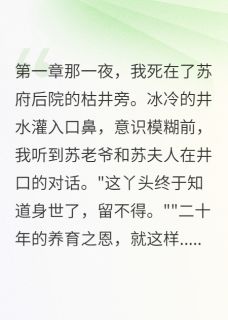小说主人公是小桃谢凛的小说叫《世子跪雪夜:挖我十年酒》,该文文笔极佳,内容丰富,内容主要讲述: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那一片狼藉,尤其是那件染血的嫁衣和散开的酿酒方子。死一般的寂静里,只有小桃压抑的、绝望的啜泣声,还有我……
《世子跪雪夜:挖我十年酒》精选:
##我埋了十年酒,他烧我嫁衣>我在谢凛窗外的银杏树下埋了第十坛酒。
>他正为柳如萱点燃满城烟花,火光照亮我绣嫁衣时熬坏的双眼。
>柳如萱的珠钗却“意外”落在我院中,引他撞见我“偷窃”的现场。
>他冷眼旁观我被押走:“苏婉,你让我恶心。”>离府那日,
柳如萱的婢女故意撞翻我的包袱。>染血的嫁衣和十年酿酒方散落满地,
谢凛突然死死攥住我的手腕。>“这些是什么?”他声音发颤。
>我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:“谢世子,是垃圾。”>后来他冒雨追到渡口,
却只看见我焚烧嫁衣的火光。>火焰中,那张未绣完的鸳鸯帕格外刺眼。
>——那是当年他高烧时,我连夜绣好为他拭汗的方帕。---第十坛了。
指尖擦过粗粝的陶坛,冰凉的泥土气息混着若有似无的酒香,钻进鼻腔。
我把它放进新挖的坑里,深秋的寒气顺着指尖往上爬,冻得骨头缝里都透着酸涩。
填土的时候,手控制不住地发抖,铁锹的木柄磨着掌心,钝钝地疼。十年了。每一坛酒,
都藏在这棵老银杏盘虬的根须之间,藏在他书房的窗棂之下。风一吹,
金黄的叶子就打着旋儿落下来,沙沙地响,像是替我把那些不敢出口的话,一遍遍说给他听。
“……阿凛,今年的新酒,梅子熟得正好……”土坑渐渐被填平,
最后一点酒坛的轮廓也消失不见。我直起身,腰背僵硬得像块枯木。
目光习惯性地投向那扇熟悉的窗,烛火通明,映着窗纸上两个清晰的身影。靠得极近。
心口猛地一缩,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。几乎同时,尖锐的破空声撕裂了寂静的夜幕!
“咻——嘭!”赤金的、明蓝的、银白的……无数光点尖啸着蹿上墨黑的天空,轰然炸裂。
绚烂到极致的光华瞬间泼洒下来,将整个侯府、连同我站立的这方小小院落,
都照得亮如白昼,纤毫毕现。光太亮了,刺得我下意识闭了闭眼。再睁开时,
那窗纸上的人影更清晰了。女子窈窕的身姿微微前倾,似乎在指点着窗外的盛景。而他,
谢凛,就站在她身后半步,微微低着头,那个角度……那个角度,温柔得能溺死人。
烟花的光明明灭灭,映在我脸上,滚烫。可眼睛深处,
那熬了无数个深夜绣嫁衣落下的酸涩与干痛,却在此刻尖锐地复苏,针扎一样密密地刺上来,
逼得眼底一阵湿热。真好看啊。我仰着头,望着那片不属于我的喧嚣与璀璨,
喉咙里堵得发不出一点声音。为了柳如萱的生辰,他竟点了这满城的烟火。也是,
她那样的女子,柳家嫡出的**,才貌双绝,京中多少儿郎趋之若鹜,
自然值得这样倾城的绚烂。而我呢?苏婉,一个寄居在侯府的表**,
一个卑微的、只敢把心意埋进土里的可怜虫。最后一声巨大的轰鸣在天际炸响,
拖着长长的、不甘的余烬,归于死寂。黑暗重新温柔地覆压下来,
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,盖过了泥土和酒的气息。整个世界,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,
还有胸腔里那颗被烟花炸得血肉模糊的心,还在微弱地跳动。我狠狠抹了一把脸,
指尖一片冰凉的湿意。转身,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,一步步挪回我那间偏僻的小院。每一步,
都像是踩在烧红的炭火上。那满天的华彩,那窗上的剪影,一遍遍在脑子里回放,挥之不去。
推开院门,吱呀一声,在寂静里格外刺耳。我反手掩上门,背靠着冰冷的门板,
才觉得浑身脱力,一点点滑坐在地上。黑暗中,只有自己的心跳,擂鼓一样敲打着耳膜。
不知过了多久,天边隐隐泛起蟹壳青。我扶着门板,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挪到窗边的水盆前,
掬起冷水扑在脸上。冰凉的**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。“**,**!
”急促的脚步声伴着惊慌的呼喊由远及近,是我的贴身丫鬟小桃。她猛地推开门,脸色煞白,
手里死死攥着一支珠钗,声音都在抖:“出……出事了!柳**的珠钗,
在……在我们院子里!”那支珠钗躺在小桃汗湿的手心里,金丝缠枝,顶端一颗硕大的东珠,
在昏暗的晨光里兀自流转着冰冷的光晕。正是柳如萱昨日簪在发间,
引得满堂宾客赞叹的那一支。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头顶。“怎么会在这里?
”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。“不知道啊**!”小桃急得快哭了,“早上洒扫的婆子,
就在……就在院门口那丛冬青底下发现的!现在……现在柳**那边丢了东西,
正闹着要查呢!”话音未落,院门外已经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刻意拔高的议论声。
“就是这儿?搜仔细点!”“柳**那支钗可是御赐的,价值连城,
若真被哪个眼皮子浅的顺了手……”“哼,有些人啊,寄人篱下久了,
难免心思就歪了……”声音尖刻,毫不掩饰地穿透薄薄的门板,像淬了毒的针,
一根根扎进耳朵里。小桃气得浑身发抖:“她们血口喷人!”我按住小桃的手,
冰凉的手指却止不住地发颤。这不是意外。柳如萱的珠钗,
怎么会“恰好”掉在我这偏僻小院的门口?这分明是冲着我来,是一个早就设好的陷阱,
等着我踏进去。院门被粗暴地推开,两个膀大腰圆的婆子闯了进来,
后面跟着几个柳如萱房里的丫鬟,个个脸上带着看好戏的刻薄。为首那个婆子三角眼一吊,
目光像毒蛇的信子扫过我的脸,最后钉在小桃紧握的手上。“哟!这不是我们柳**的钗吗?
”她尖声叫道,猛地扑过来,一把从小桃手里夺过珠钗,高高举起,“人赃并获!苏**,
您还有什么话说?这御赐之物也敢偷?”“你胡说!是它自己掉在我们院门口的!
”小桃扑上去想抢回来,却被另一个婆子狠狠推搡在地。“自己掉的?
这么巧就掉在你家主子门口?”那婆子嗤笑一声,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,
“当我们都是傻子不成?定是昨儿个夜里,趁着府里乱糟糟的放烟火,有人手脚不干净,
摸黑溜进我们**院里偷了来!真是好大的胆子!”污言秽语像冰雹一样砸下来。
我站在原地,手脚冰凉,血液似乎都凝固了。所有的辩解在对方蓄谋已久的构陷面前,
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看到院门口围拢的人越来越多,那些目光,有鄙夷,有好奇,
有幸灾乐祸……像无数根芒刺,扎得我体无完肤。就在这时,人群忽然安静下来,
自发地向两边分开,让出一条通道。他来了。谢凛穿着一身墨色锦袍,身姿挺拔,
步履间带着惯有的冷峻。柳如萱依偎在他身侧,眼圈微红,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,
看向我的眼神却飞快地掠过一丝冰冷的得意。“凛哥哥,
”柳如萱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,娇弱地拉了拉谢凛的衣袖,
“就是那支钗……是皇后娘娘赏的,我平日最是珍视……没想到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,
只用那双盈盈含泪的美目望着谢凛。谢凛的目光扫过婆子手中高举的珠钗,
又缓缓移到我脸上。那双深邃的眼眸,曾经是我小心翼翼珍藏的光,
此刻却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寒潭,里面翻涌着毫不掩饰的厌恶与鄙夷,冰冷刺骨,
几乎要将我冻僵。“苏婉,”他的声音不高,却像淬了寒冰的刀刃,
清晰地切割开凝滞的空气,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分量砸在我心上,
“你竟做出这等下作之事?”下作?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,狠狠烫在我的心尖上。十年,
整整十年的默默守望,小心翼翼的靠近,所有那些深埋地下的酒坛,
所有那些深夜灯下熬红眼睛绣下的针脚……在他眼里,原来只配得上“下作”二字?
血液瞬间冲上头顶,又在下一秒褪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彻骨的寒冷和麻木。
喉咙里像是堵了滚烫的炭,灼烧得生疼,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辩解?在他这样的眼神下,
在柳如萱精心布置的这场戏里,任何言语都只会显得更加可笑和卑贱。
“不……”小桃挣扎着爬起来,带着哭腔喊,“世子爷明鉴!不是我家**!是有人陷害!
”“陷害?”谢凛薄唇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,那弧度里没有一丝温度,只有浓浓的讽刺,
“证据确凿,还敢狡辩?人赃并获,难道这钗是自己长了脚,跑到你们这院子里来的不成?
”他的目光转向那两个婆子,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,“还愣着做什么?偷窃御赐之物,
按府规该当如何处置?”为首那个三角眼的婆子立刻精神抖擞,高声应道:“回世子爷,
按规矩,当杖责二十,再交由柳**发落!”“那就拖下去!”谢凛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,
冷硬得像块生铁。他甚至不再看我,仿佛多看一眼都会脏了他的眼睛。那冰冷的侧脸线条,
在晨光里像一尊毫无感情的玉雕。“世子爷!冤枉啊!”小桃哭喊着扑过去,
想抱住谢凛的腿,却被旁边的家丁粗暴地架开。“**!**!”她撕心裂肺地朝我哭喊。
两个粗壮的婆子立刻狞笑着扑上来,铁钳般的手死死抓住了我的胳膊。
粗糙的手指像砂纸一样磨着我的皮肤,带来一阵**辣的疼。巨大的屈辱感瞬间淹没了我,
身体被她们蛮横地拖拽着向外走,脚步踉跄,几乎站立不稳。裙裾扫过冰冷的地面,
沾上肮脏的尘土。周围那些目光,那些窃窃私语,像无数根芒刺,狠狠扎进我的皮肉里。
经过谢凛身边时,那股熟悉的、带着冷冽松香的气息拂过鼻尖。我下意识地微微偏过头,
视线正好对上他垂下的眼睫。那浓密的睫毛下,那双曾经无数次在我梦里出现过的眼睛,
此刻如同结了冰的深湖。没有愤怒,没有探究,只有一种彻底、纯粹的嫌恶。
那眼神像淬了剧毒的冰锥,精准无比地刺穿了我仅存的一点支撑。原来,十年的光阴,
十年的心意,在他眼中,不过是一滩令人作呕的污秽。喉头猛地涌上一股浓重的腥甜,
又被我死死咽了回去。我放弃了挣扎,任由那两个婆子如拖拽一件破败的垃圾般,
将我拖离了这个院子。每一步,都踏在碎裂的心尖上。……杖责并没有真的落下二十下。
或许是执刑的管事婆子也觉出几分蹊跷,或许是柳如萱觉得这戏演得差不多了,
需要留点余地。打到第十下时,一个丫鬟急匆匆跑来,在管事婆子耳边低语了几句。
那婆子挥了挥手,示意停下。“算你走运!柳**心慈,念在你终究是侯府表**的份上,
免了剩下的杖子!”婆子粗声粗气地说着,眼神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,“不过,
柳**说了,侯府是留不得你了。赶紧收拾东西,今日就离府!”粗糙的竹杖落在皮肉上,
每一下都带着沉闷的钝响,带来炸裂般的剧痛。冷汗瞬间浸透了里衣,黏腻地贴在背上。
我死死咬着下唇,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,硬是一声没吭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
试图用另一种尖锐的疼痛来对抗这铺天盖地的屈辱和身体上的折磨。十下。骨头像是散了架,
腰臀以下一片**辣的麻木与钻心的痛楚交织。当那个传话的丫鬟出现,
婆子宣布柳如萱“心慈”的赦令时,我只觉得一股冰冷的讽刺直冲头顶。心慈?
她不过是要把我彻底赶走,还要在谢凛面前维持她善良大度的假面罢了。两个婆子架着我,
几乎是把我半拖半拽地扔回了那间偏僻的小院。身体重重摔在冰冷的地面上,震得伤口剧痛,
眼前阵阵发黑。“**!”小桃哭喊着扑过来,手忙脚乱地想扶我起来,
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我脸上,滚烫。“别……别动我……”我倒抽着冷气,
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,“……收拾东西……我们走……”小桃哭得更凶了,却不敢再碰我,
只能胡乱地用袖子擦着眼泪,踉跄着爬起来去收拾我们那点可怜的家当。我趴在冰冷的地上,
粗重地喘息着,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身后的伤,疼得浑身哆嗦。
目光空洞地望着眼前一块斑驳的地砖,上面沾着一点新蹭上去的泥土。十年,就这样结束了。
像一场荒唐的梦,最后以最不堪的方式惊醒。不知过了多久,小桃终于收拾好了。
她吃力地搀扶着我,几乎是把我整个人的重量都架在她瘦小的肩膀上,
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出房门。小小的包袱挎在她另一侧手臂上,
里面是我们主仆二人在这侯府十年间所有的、微薄的积蓄和几件换洗衣物。
深秋的风卷着枯叶,刮在脸上生疼。阳光惨白,
照得侯府那些熟悉的亭台楼阁都透着一股冰冷的陌生感。我们沿着偏僻的回廊往后角门走,
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刚转过一处假山,远远就看见一行人迎面走来。
柳如萱被一群丫鬟婆子簇拥在中间,如同众星捧月。她换了一身簇新的鹅黄色锦缎衣裙,
衬得肌肤胜雪,发髻间簪着那支失而复得的东珠步摇,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,流光溢彩。
看到我们,她脸上立刻浮现出恰到好处的惊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“苏妹妹?
”她脚步轻快地走上前,声音柔婉,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刀子,细细地刮过我的狼狈,
“这是……要走了?唉,出了这样的事,妹妹心里定然也不好受。凛哥哥也是按规矩办事,
妹妹千万别怨他。”她说着,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小桃臂弯里那个小小的、瘪瘪的包袱。
“柳**,”我强忍着身体的剧痛和翻涌的恨意,声音低哑却努力维持着最后一点平静,
“事已至此,多说无益。请让路。”柳如萱却仿佛没听见,反而又往前凑了半步,
离小桃更近了。她脸上带着一种虚伪的关切,目光却紧紧锁着那个包袱,
嘴角勾起一丝极浅、极冷的弧度。“妹妹此去,路途遥远,可要当心身体啊。
这点子东西……”她拖长了语调,忽然,她身边一个身材壮实的粗使丫鬟猛地往前一挤,
肩膀“不经意”地重重撞在了小桃挎着包袱的手臂上!“啊!”小桃猝不及防,
本就吃力地架着我,重心不稳,惊呼一声,整个人连同我一起被撞得趔趄着向旁边倒去。
“哗啦——”包袱散开,里面的东西瞬间倾泻而出,滚落在冰冷的石板地上。
几件半旧的素色衣裙,几块散碎的银角子,一个褪了色的木梳盒子……还有,
那件叠得整整齐齐、却再也无法避开的——大红嫁衣。鲜艳夺目的红绸,
在惨淡的秋阳下刺得人眼睛发疼。上面精心绣着的金线凤凰、缠枝牡丹,
每一针每一线都浸透了我无数个夜晚的心血和痴念。更刺目的,是衣襟和袖口处,
几处深褐色的、早已干涸凝固的暗沉血渍!那是昨夜杖责时,我死死咬破嘴唇,滴落上去的。
旁边,还散落着一本泛黄的册子,纸张粗糙,
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娟秀的小字——是我这十年来,一次次改良、一次次尝试,
记录下的所有酿酒心得和方子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。所有声音都消失了。风停了,
连落叶都悬在半空。柳如萱脸上的得意僵住了,
随即扭曲成一种混杂着震惊和嫉恨的复杂表情。她身后的丫鬟婆子们,全都像被施了定身咒,
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那一片狼藉,尤其是那件染血的嫁衣和散开的酿酒方子。
死一般的寂静里,只有小桃压抑的、绝望的啜泣声,还有我粗重而痛苦的喘息。
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中,一道冰冷的、裹挟着巨大压迫感的身影,
像一道撕裂空气的黑色闪电,猛地冲到了我的面前!手腕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攥住!
力道之大,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。剧痛让我眼前一黑,闷哼出声。
一股熟悉的、带着凛冽松香的气息强势地笼罩下来。我被迫抬起头,对上了一双眼睛。
那是谢凛的眼睛。可那里面,不再是方才的冰冷嫌恶,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审判。
那双深不见底的寒潭,此刻掀起了滔天的巨浪!
惊愕、混乱、难以置信……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近乎恐慌的震动!
他的脸色在秋阳下白得吓人,薄唇紧抿成一条僵硬的直线,
目光死死地盯在地上那件刺目的红嫁衣和散落的酿酒方子上,
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、也最令他惊骇的景象。
“这些……”他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,
带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无法控制的颤抖,每一个音节都在空气里裂开,
“……是什么?”手腕上传来的剧痛,骨头仿佛在哀鸣。我看着他眼中那片混乱的风暴,
看着他脸上褪尽的血色,心底那片早已冻结的荒原上,竟奇异地生不出一丝波澜。十年。
三千多个日夜的卑微守望,无数个深夜灯下熬红的眼睛,
无数次在银杏树下悄悄埋下的祈盼……最终换来的,是冰冷的杖责,是当众的羞辱,
是“下作”的定论,是此刻他这迟来的、荒谬的、带着颤抖的诘问。“这些是什么?
”我慢慢地吸了一口气,冰冷的空气刺得肺腑生疼。然后,用尽全身仅剩的力气,
抬起另一只没有被他钳制的手,冰冷的手指,一根,一根,
缓慢而坚定地掰开他紧攥在我腕上的、那几根僵硬如铁的手指。他的手指冰凉,
甚至比我的指尖还要冷。我能感觉到他指节在微微发抖,带着一种巨大的、失控般的力道,
似乎想重新攥紧,又似乎被我的动作彻底惊住,僵在了那里。当最后一根手指被我掰开,
那只曾经支撑我所有幻想、此刻却只带来无尽痛楚的手,终于无力地垂落下去。
我收回自己重获自由、却已是一片青紫淤痕的手腕,看也没看它一眼。
目光平静地掠过地上那片狼藉——那染血的嫁衣,那散落的酿酒方子,
那是我十年青春和所有痴心妄想凝结成的、最不堪的碎片。最后,
视线才落回谢凛那张失魂落魄、写满惊涛骇浪的脸上。他的眼神依旧死死锁着地上的东西,
仿佛要将其洞穿。我扯了扯嘴角,牵动脸上僵硬的肌肉,
露出一个极其微弱的、近乎虚无的弧度。那笑容里没有温度,没有嘲讽,
只有一片彻底的、死寂的荒芜。“谢世子,”声音嘶哑,像砂纸磨过粗粷的木头,
却异常清晰地穿透了凝固的空气,砸在每一个人耳中,也砸在他骤然收缩的瞳孔上。
“是垃圾。”两个字,轻飘飘的,却带着千钧之力,将地上那些承载着我所有心血的碎片,
连同他那迟来的震动,一同碾入尘埃。说完,我甚至没再看他一眼。
身体的剧痛如同附骨之蛆,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烧红的刀尖上,骨头缝里都渗着寒意。
我咬紧牙关,用尽全身力气,将自己所有的重量压在小桃那瘦小却异常坚定的肩膀上。
“小桃,”声音低哑,几乎是从齿缝里挤出来,“扶我走。”小桃脸上还挂着泪,
眼睛却亮得惊人,用力地点头:“嗯!**,我们走!”我们主仆二人,一个伤痕累累,
一个泪痕未干,相互搀扶着,踉跄却异常决绝地,一步一步,从谢凛僵立如石像的身旁走过,
从柳如萱那震惊又嫉恨的目光中穿过,
从那些噤若寒蝉的丫鬟婆子围成的、令人窒息的路障中挤了出去。身后,
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。那件染血的嫁衣,那些散落的方子,像被遗弃在荒野的祭品,
躺在冰冷肮脏的地面上,无人敢动。我没有回头。一次也没有。……江南的深秋,
雨总是缠绵。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,笼罩着渡口,也笼罩着船舷。河水浑浊,
拍打着木质的船身,发出沉闷的哗哗声,带着一种催人离开的急迫。小桃撑着伞,
小心地遮在我头上,自己半边身子却露在雨里。她看着船工解开最后一根系在岸桩上的粗绳,
眼圈又红了,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:“**,真的……不等舅老爷的信儿了?
侯府那边……”“不等了。”我打断她,声音平静无波,目光越过湿漉漉的船舷,
投向烟雨朦胧的河面。侯府?那个地方,连同里面的人,
都早已被埋葬在昨日那场冰冷的屈辱里,埋葬在谢凛那句“下作”的审判中。
“江南的宅子已经收拾好了,舅舅会派人来接应。”船身微微一震,
缓缓离开了湿滑的石砌渡口。岸上送行的人影在雨幕中迅速模糊、变小。就在这时,
一阵急促到近乎疯狂的马蹄声,如同密集的鼓点,撕裂了雨幕的沉闷,由远及近,
狠狠砸在每一个人的耳膜上!“嘚嘚嘚——嘚嘚嘚——”一匹黑色的骏马,
如同离弦之箭般冲上码头!马背上的人影被雨水浇得透湿,墨色的锦袍紧贴在身上,
勾勒出紧绷的线条。他甚至来不及勒停坐骑,在距离岸边还有几步之遥时,
竟直接从狂奔的马背上滚落下来!“砰!”沉重的身体砸在泥泞湿滑的码头上,
溅起一片浑浊的水花。“**!是……是世子爷!”小桃惊骇地捂住了嘴,失声叫道。是他。
谢凛。他挣扎着从泥水里爬起来,雨水顺着他凌乱的黑发往下淌,狼狈不堪,
脸上、手上都蹭破了皮,沾满了污泥。他踉跄着冲向水边,
目光死死地锁住我们这艘已经离岸数丈的船,那眼神里,
是前所未有的疯狂、绝望和一种几乎要将人焚烧殆尽的恐惧。“苏婉——!
”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,声音被风雨撕扯得破碎不堪,却带着一种穿透灵魂的凄厉,“停下!
船停下——!”“婉儿——!回来——!”“你听我解释——!”他嘶喊着,踉跄着,
不顾一切地想要冲进冰冷的河水里追上来。岸上立刻有随从扑上去死死抱住他,
阻止他疯狂的行径。他在泥水里挣扎扭打,像个彻底失控的疯子,雨水、泥浆糊满了他的脸,
那嘶吼声在风雨中显得那么绝望,那么徒劳。船,在船工有力的撑篙下,
正坚定地驶向河道中央,离岸边越来越远。冰冷的雨丝扑在脸上,带着深秋刺骨的寒意。
我静静地站在船头,雨水顺着鬓角滑落,视线穿过迷蒙的雨幕,
落在那岸上泥泞中挣扎嘶吼的身影上。心头那片早已冰封的荒原,
竟奇异地没有掀起一丝涟漪。没有恨,没有怨,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。
只余一片沉寂的、近乎虚无的疲惫。解释?多么苍白无力的两个字。当那冰冷的杖子落下,
当他吐出“下作”那两个字时,
当那染血的嫁衣和酿酒方子如同垃圾般散落在他脚下时……一切的解释,
都早已被那满城的烟花、那冰冷的眼神、那毫不留情的审判,烧成了灰烬。“小桃,
”我收回目光,声音在风雨中显得异常平静,“把那个包袱拿来。”小桃愣了一下,
随即明白了什么,飞快地跑回船舱,
抱出了那个在侯府门口散落、又被她重新草草收拾起来的包袱。那件刺目的红,
即使在昏暗的雨中也无法被完全掩盖。我接过包袱,解开。
手指触碰到那冰凉的、带着血渍的红绸时,指尖几不可察地蜷缩了一下。然后,我平静地,
将那件承载了我所有少女幻梦、也浸透了我最后绝望与耻辱的嫁衣,抖开。
大红的绸缎在灰暗的天地间骤然展开,像一片燃烧的血色旗帜。
金线绣成的凤凰和牡丹在雨水的浸润下,黯淡了华彩,却依旧刺眼。
衣襟袖口那深褐色的血渍,更是触目惊心。岸上的嘶吼声似乎停顿了一瞬,
谢凛挣扎的动作也僵住了,隔着越来越大的雨幕,他死死地盯着那件被抖开的红裳,
瞳孔骤然收缩到极致,脸上是彻底崩溃的惊骇。我没有看他。只是弯腰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