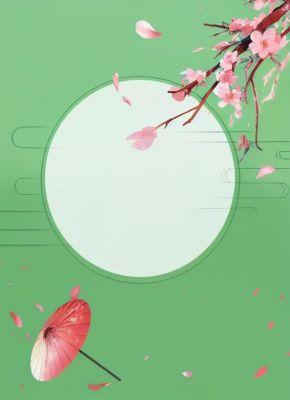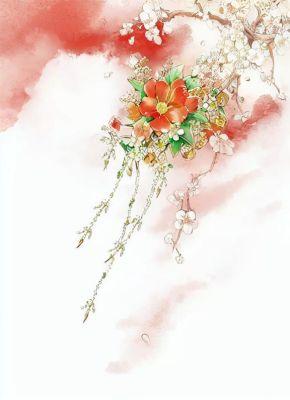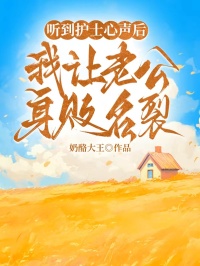在未我花生的小说《晚潮与旧书》中,林夏沈砚阿芷是一个普通人,但他注定要成为改变世界的英雄。被选中保护一个古老的神秘遗物,林夏沈砚阿芷踏上了一场充满奇幻和冒险的旅程。他将面对邪恶势力的追逐和自己内心的挣扎,同时也发现了自己隐藏的力量和使命。老头这时抬头看了她一眼,烟卷在嘴角抖了抖:“那本书啊,放这儿三年了,没人要。”“为什么?”林夏问。“晦气。”老头吐出个烟……将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世界。
《晚潮与旧书》精选:
1第一章:鼓浪屿的旧书林夏第一次见到那本旧书,
是在鼓浪屿岛北一家快要倒闭的旧货店里。那天是台风过境后的第三个下午,
她跟着导航在迷宫似的巷子里绕了二十分钟,裤脚还沾着海边溅起的咸湿水汽。
旧货店的木门掉了半块漆,门楣上“老林杂货”的招牌歪歪斜斜,
风一吹就发出“吱呀”的**,像个喘不过气的老人。店主是个穿蓝布衫的老头,
正蹲在门口修一把断了腿的藤椅,看见她进来,头也没抬,只指了指墙角:“随便看,
下周就拆了。
店里堆着五花八门的旧物:缺了口的瓷碗、生锈的铜炉、印着“鼓浪屿留念”的铁皮饼干盒,
还有一摞摞码在地板上的书。林夏是来岛上写生的,原本想找个老相框当道具,
目光却被最底下那本压得变形的书勾住了。书皮是深棕色的硬壳,边缘磨得发毛,
烫金的书名“潮汐手记”只剩下“潮”和“记”两个模糊的字,书脊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,
墨水晕开了大半,勉强能认出“沈”和“1987”的字样。她蹲下来,指尖刚碰到书皮,
就觉得一阵凉意从指尖窜上来——不是旧物的霉味,而是像刚从海边捞上来的湿冷。
老头这时抬头看了她一眼,烟卷在嘴角抖了抖:“那本书啊,放这儿三年了,没人要。
”“为什么?”林夏问。“晦气。”老头吐出个烟圈,“前两年有个游客想买,
刚翻开第一页,外面就打雷,把门口那棵凤凰木劈了个大口子。后来我自己想翻翻,
一打开就头疼,跟被海水呛了似的。”林夏笑了笑,没信。
她从小就对旧东西有种莫名的执念,总觉得每件老物件里都藏着一段没说完的话。
她把书抱起来,书不厚,却比看起来重,像是夹着几块小石头。“多少钱?
”老头摆了摆手:“拿走吧,算我送你了。赶紧把这‘麻烦’送走。”走出旧货店时,
夕阳正把巷子染成橘红色,海风卷着凤凰花的花瓣落在书皮上。林夏把书抱在怀里,
忽然觉得怀里的书好像轻轻动了一下,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翻了个身。回到租住的民宿,
林夏把书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。民宿在岛南的半山腰,推开窗就能看见大海,
潮声像永不停歇的背景音。她煮了杯热咖啡,坐在窗边,终于翻开了那本《潮汐手记》。
2第二章:潮汐里的阿芷第一页是空白的,
只有右上角用铅笔写着一行极淡的字:“今日潮时,寅时三刻,潮高八尺。”字迹清瘦,
带着点潦草的锐气。第二页开始,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,偶尔夹着几幅铅笔素描,
画的都是海边的景象:涨潮时的浪花、退潮后的礁石、停在滩涂上的小渔船,
还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,坐在礁石上,背对着画者,手里拿着一个贝壳。
作者的名字在第三页的落款里出现了——沈砚。笔记里记的大多是潮汐的变化:“三月十七,
大雨,潮涨至码头石阶第三级,捡得一只断了线的风筝”“四月廿二,晴,
退潮后滩涂上有很多花蛤,阿芷说要煮成汤”“五月初五,端午,潮平,和阿芷去看龙舟,
她笑的时候,辫子上的红绳晃得人眼晕”。林夏越看越入迷,
仿佛跟着沈砚的文字回到了1987年的鼓浪屿。笔记里的“阿芷”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,
从最初的“阿芷说”“阿芷喜欢”,到后来的“今日和阿芷在海边坐了一下午,
她教我认海星”“阿芷送了我一个海螺,说能听到远方的声音”。
字里行间的温柔像潮水一样漫上来,林夏甚至能想象出那个叫阿芷的女孩,扎着红绳辫,
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,蹲在滩涂上,把捡到的贝壳递到沈砚手里。看到一半时,
窗外的潮声忽然变大了,像是有浪头要拍进窗里来。林夏抬头看了一眼,海面平静得很,
夕阳正慢慢沉进海里,把海水染成一片金红。她低下头,继续往下翻,翻到第27页时,
字迹忽然变得潦草起来,墨水也晕得厉害,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:“六月初三,阴,
潮时不明。阿芷说要走了,去上海,她爸爸在那边找了工作。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,
她说不知道。海边的风很大,把她的头发吹乱了,她哭了,我没敢看。”下一页,
画着一只空了的礁石,礁石上放着一个海螺,螺口朝着大海。
旁边的文字只有一行:“今日无潮。”再往后,笔记的内容变得混乱,
大多是重复的潮时记录,偶尔夹着几句破碎的话:“阿芷的信,还没到”“今日潮高九尺,
比昨日高一寸”“海边的风筝又飞起来了,不是她的那只”“潮涨潮落,人怎么就不回来了?
”最后一页的日期是1987年8月15日,只有一句话,字迹被泪水晕得模糊不清,
勉强能辨认:“今日潮退,再也没等到她。”林夏合上书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,闷闷的。
她看向窗外,夜色已经漫上来,潮声比刚才更响了,像是有人在海边哭。她伸手摸了摸书皮,
那股湿冷的感觉又回来了,这一次,她好像真的闻到了海水的味道,带着点咸涩的腥气。
那天晚上,林夏做了个梦。梦里她站在一片陌生的海滩上,天色灰蒙蒙的,像是要下雨。
潮水正在上涨,浪花拍打着礁石,发出“哗哗”的声音。不远处的礁石上,
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男生,背对着她,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。她走过去,
想问他是不是沈砚,刚开口,男生忽然转过头来——他的脸模糊不清,像是被雾气笼罩着,
只有手里的书看得很清楚,正是那本《潮汐手记》。“她不会回来了。”男生说,
声音像潮水一样,忽远忽近。“谁?阿芷吗?”林夏问。男生没回答,只是把书合上,
朝着大海走去。潮水很快没过了他的脚踝、膝盖、腰……直到整个人被海水吞没,
只剩下那本《潮汐手记》漂浮在海面上,被浪头卷着,慢慢漂向远方。林夏想伸手去抓,
却发现自己的脚像被钉在了沙滩上,动弹不得。这时,她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她的名字,
声音很轻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她猛地睁开眼,窗外的天已经亮了,潮声还在继续,
只是比夜里温柔了些。她摸了摸额头,全是冷汗,怀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那本《潮汐手记》,
书皮湿淋淋的,像是刚从海里捞上来。“奇怪。”林夏嘀咕了一句,把书放在书桌上,
去卫生间洗漱。等她回来时,忽然发现书翻开了,
正好停在最后一页——1987年8月15日那页。而原本空白的页脚,
多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,字迹和沈砚的一模一样:“明日潮时,辰时一刻,潮高七尺。
”林夏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来。她拿起书,仔细看那行小字,墨迹还很新,像是刚写上去的。
她又翻回前面,发现之前那些记录潮时的页面上,
有些日期旁边多了小小的批注:“今日潮时准确”“潮高差了一寸”“阿芷喜欢今天的浪”。
她忽然想起旧货店老头说的话——这本书“晦气”,会让人头疼,会引来打雷。
现在她才明白,不是晦气,是这本书里的人,还没放下。接下来的几天,
林夏成了鼓浪屿上最准时的“观潮人”。每天早上,她都会先翻开《潮汐手记》,
看看沈砚有没有留下新的批注,然后拿着笔记本去海边,记录当天的潮时和潮高,
和笔记里的记录对比。她发现,沈砚的记录几乎分毫不差,像是他能和大海对话一样。
有一天,她在笔记里看到一句新的批注:“阿芷喜欢在退潮后的礁石上找小螃蟹。
”那天下午,她特意等到退潮,沿着滩涂往前走,果然在一块大礁石后面,
看到了几只小小的石蟹,横着爬来爬去。她蹲下来,刚想伸手去抓,
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孩的笑声,清脆得像风铃。她猛地回头,身后空无一人,
只有浪花拍打着礁石,像是在嘲笑她的幻觉。“沈砚?”她试探着喊了一声,
声音被海风卷走,没留下一点痕迹。那天晚上,她在《潮汐手记》的空白页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