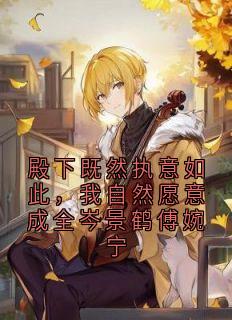绘卷画写的《相公宁上战场送死,也要与我和离》的情节跌荡起伏,扣人心弦,人物生动鲜活,让人过目不忘!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古代言情作品了!主要讲述的是:从此男婚女嫁,各不相干。”屋子里静得可怕。我看着桌上的文书,攥紧了袖子。我自幼失怙,在舅舅家长大。舅妈算计我的婚事不是一……
《相公宁上战场送死,也要与我和离》精选:
夫君战死沙场的噩耗传来后。是小叔子谢砚舟力排众议,将我这个寡嫂接回京中照料。
三年来,他克己守礼,事事周全。满京城无人不赞他一句君子端方。我也一度以为,
这深宅大院中。终是有一隅安身之所。直到我收下江南苏家公子的玉佩,浅笑着对他说。
“二叔,苏公子为人诚挚,我...想试着开始新的生活。”他当时端着茶盏的手稳如磐石,
颔首应了声。“但凭嫂嫂心意。”可当夜,他却带着一身夜露的寒凉,
兀自推开了我未栓的门闩。平日里清冷如玉的嗓音,浸满了压抑的风暴。“新生活?“嫂嫂。
”他冰凉的指尖掠过我的下颌,气息迫近。“我不同意。”1我嫁给谢家大郎的时候,
他正闹着投军。谢母哭着把我拉到他面前。“砚礼,你是家中长子,
非要去那刀剑无眼的战场上,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?“你说你要娶妻,我们也给你娶了,
珍娘是个好的,你就好好在家过日子吧。”谢大郎的目光在我脸上打了个转儿,嗤笑一声。
“凭她?“一个破落户家里的女儿,如何能与沈**比?”江州沈家,我是知道的。
沈家家境殷实,两位公子都是读书的好苗子。沈**行三,生得一副好皮囊,
家里又是宠着娇养着长大,我自是比不上的。谢母闻言,身子晃了晃。“砚礼,
沈家不是我们能攀附的起的,你莫要再执迷不悟....”谢大郎长袖一挥,冷冷道。
“只要我去投军,就必能有所建树。“等我有了功名,你又怎知沈**不会心悦于我?
”说罢,他又从行囊中取出一纸文书放在桌上。“这是和离书。“我已签好了字,
从此男婚女嫁,各不相干。”屋子里静得可怕。我看着桌上的文书,攥紧了袖子。
我自幼失怙,在舅舅家长大。舅妈算计我的婚事不是一天两天。如今若被休弃回去,
只怕转头就要被塞给城东死了三个老婆的张员外做填房。指尖在袖中掐得生疼,
我抬头迎上谢大郎不耐的目光。决定为自己争一把。“我不和离。”声音不大,
却让满室皆静。谢母止了哭泣,谢大郎皱起眉。“你说什么?”我向前一步,
目光扫过那封刺目的和离书。“我说,我不和离。“谢家既明媒正娶我进门,
我便生是谢家的人,死是谢家的鬼。”谢大郎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
“你当我是在同你商量?”“自然不是。”我平静道。“大公子志向远大,珍娘不敢高攀。
只是......”我故意顿了顿,看向面色苍白的谢母。“婆母年迈多病,大公子这一走,
家中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。“若我也走了,岂不是要婆母独自撑起这个家?
”谢家祖上原是江州有名的富户。太爷爷曾官至四品,在城南置下五进的大宅,良田百顷。
只是到了谢父这一代,家道已然中落。为谢大郎娶亲,几乎掏空了家底。
谢家二郎是个清风霁月的读书人。已经参加过院试考了秀才,
可惜却因家中境况不得不暂时搁下笔墨。赴省城乡试,光是驿马、食宿、结保,
便要几十两银子。更别提考前需要拜名师、买时文集,哪一样不要钱?
家中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子,身量未足,像一株需要依附的藤蔓。谢大郎沉默良久,
终于嗤笑一声。“随你。”他转身拎起行囊,大步流星地跨出门去,再没回头。
我松了一口气。弯腰拾起那封和离书,小心叠好收进袖中。
2我顶着谢家大嫂的名头住了下来。谢母的活计,尽数落在我的肩上。天未亮时我便起身,
米缸见了底,只能多掺些薯芋,让粥看起来稠些。随后便是缝补浆洗,
十指在常在凉水里泡得发红。谢母几次要来帮我,都被我挡了回去。我从小寄人篱下,
这些活计都是做惯了的。况且谢母年轻时亏了身子,如今咳嗽起来整夜难眠,
我又怎忍心让她再操劳。让我没想到的是谢二郎。每次我起来时,他就已经在院中劈柴。
晨光熹微中,他褪去了平日里常穿的青衫,只着一件单薄的短打。抡起斧子时,
臂膀的线条骤然绷紧,竟能看出清晰的肌肉轮廓。肩背虽不厚阔,却舒展而有力。随着动作,
脊骨在薄薄的衣衫下若隐若现。这实在不像一个终日与诗书为伴的秀才郎。
我一时竟忘了挪开眼。待反应过来时,只觉一股热气腾地涌上脸颊,烧得耳根都发烫。
谢二郎面容清冷,嗓音微凉。“可是吵到嫂嫂了?”我慌忙垂下眼。“没,
没有吵到......“我去看看粥。”几乎是落荒而逃。自那日后,我便稍晚一刻钟起来,
怕再遇见上次那般让人尴尬的场景。谢二郎倒没受影响,檐下总是摆放着码的整整齐齐的柴。
还有家里的水缸,总是满的。最重的米袋也被人悄悄挪到了我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日子在清贫中流淌,像屋檐下的细雨,无声却绵长。我开始觉得,
这清贫却有人间烟火的谢家。才是我真正的归处。直到谢大郎的死讯传来。3那日,
我同往常一般去村东头的河边浣洗衣物。谢砚欢怀里也抱着一个木桶,
脚步轻快地跟在我身后。河水哗哗,伴着此起彼伏的棒槌声。“听说北边打仗,死了好些人。
”旁边刘婶一边用力捶打着衣物,一边对身旁的妇人说道。“我娘家侄子在县衙当差,
昨日回来说,这几日就要往咱们这边送阵亡文书了。”我的心猛地一沉,棒槌差点脱手。
一旁的妇人朝我和砚欢努努嘴。“谢家大郎不是也去投军了?
“你说会不会....”她说着,目光似有若无地朝我这边瞥了一眼。砚欢的手微微发抖,
手中的小衣顺着水流漂走。我定了定神,涉水几步将衣服捞了回来。
不知是不是河水太过清凉,我的指尖竟然有些僵硬。“嫂嫂....”砚欢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我轻轻捏了捏砚欢的手,将她往身边带了带。“你大哥临走时说了,他去的是后勤辎重营,
安全得很。”这话是说给砚欢听,更是说给自己听。我侧过头,凑到砚欢耳边,
将声音压到最低。“莫听她们嚼舌根,跟紧嫂嫂,我们回家。”一进院门,
我便将木盆轻轻放下,径直走向西厢书房。谢二郎正在临帖。见我推门,笔尖一顿,
墨迹在纸上洇开一小团。“二叔。”我掩上门,背靠着门板,
方才在河边强装的镇定此刻消散殆尽。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轻颤。“外头,
外头都在传,北边战事惨烈......“你大哥他......”谢二郎沉默片刻,
清俊的眉宇紧锁。“嫂嫂莫慌。“我明日一早就去书院寻赵教谕,他兄长在军中任职,
或许能问到确切消息。”我点点头,也只好如此了。接下来的几日,
谢家笼罩在一片无形的阴云里。我和谢二郎默契地瞒着谢母,在她面前强颜欢笑。
就连一向活泼的砚欢也安静了下来。彼此眼神交汇时,都看到了对方眼底深藏的不安。
谢二郎托的人迟迟没有回音,我心中的不祥预感越来越重。第五日午后,我刚服侍谢母睡下。
院门外突然传来了清晰的叩门声。“此处可是谢砚礼家?”透过窗棂,
我清楚地看到两名穿着皂隶公服、腰佩朴刀的官差,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外。
谢二郎从书房快步走出。为首的官差确认了身份,
随后从怀中取出一份盖着朱红大印的文书和一个不起眼的布包。“谢砚礼于陇右道殉国,
节哀。”官差的声音平淡无波,将东西递了过来。“这是阵亡文书,以及抚恤银。
”谢二郎接过东西,久久未动。4谢母病倒了。我连夜请了大夫来看,大夫摇摇头,
只开了些调理身体的,说先将养着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舅母听说了谢大郎的死讯,
带着娘家的兄弟来谢家堵我。“珍娘,你年纪轻轻,何苦留在这儿守寡。
“我与你舅舅商量了,城东周掌柜正好是个鳏夫,前头还留下一儿一女,与你倒也般配。
”我不知周掌柜是谁,但心里明白那绝对不是个好去处。“舅母,一女不侍二夫,
我既嫁给了......”“我呸!”舅母一口唾沫吐到地上,指着我的鼻子怒骂。
“你倒是想当贞洁烈女,可惜没人给你立牌坊。“打小吃我的穿我的,
现在你表弟正等着银钱娶媳妇呢,你倒窝在这当寡妇了。“跟我走!”舅母伙着身边的男人,
拖着我就要走。我挣扎着不肯,一个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。
躲在门后的砚欢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一边哭一边往我们这边跑。“你欺负我嫂嫂,
看我不咬死你。”舅母的手腕被死死咬住,吃痛下松开了手。“哪儿来的贱丫头,竟敢咬我,
真是找死!”她抡起胳膊就要打人,却在半空中被人扼住。“你确定要在谢家撒泼?
”谢二郎清冷的声音响起,我的心竟莫名安定了一些。“我大哥为了家国战死,
你却带人前来欺辱他的遗孀。“不知县衙大人知道了,会如何处置你?”舅母脸色瞬间惨白。
谢二郎是读书人,舅母本就有些怵,再一听县衙,更是心里发慌。她指着谢二郎,色厉内荏。
“你少来吓唬我!珍娘是我养大的,你家男人死了,总不能让她守一辈子活寡吧?
”谢二郎看我一眼,旋即从袖中取出银钱,扔在了地上。
“这些算是全了往日你养我嫂嫂的情分。“以后我嫂嫂与你们聂家再无瓜葛!“还不快滚!
”舅母狠狠瞪我一眼,捡起地上的银钱就走了。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,
只剩下砚欢低低的抽泣声。**着冰凉的墙壁,脸上**辣的疼,心里却是一片荒芜。
“嫂嫂。”谢二郎的声音将我从混乱的思绪中拉回。他走到我面前,
将之前官差给的那个装着抚恤银的布包。以及自己干瘪的钱袋,一并递到了我面前。
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,声音却竭力维持着平静。“这些你拿着。”我愕然抬头,
对上他那双清冷的眸子。“大哥......不在了。“谢家不能再困着你。”他顿了顿,
喉结滚动,避开我的目光,望向门外空旷的院落。“你还年轻,不必守着这烂摊子。
不若寻个安身立命之处,开始新的生活。”砚欢缩在我怀里,哭的伤心。“嫂嫂别走,
砚欢不要你走。”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,又酸又胀。我抬起头,看向谢砚舟。
声音不大,却异常清晰坚定。“这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。”他猛地看向我,
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。我将他递钱的手轻轻推了回去。
目光扫过这虽然破败却承载了我所有归属感的小院,缓缓道。“娘需要汤药,砚欢需要教养,
你需要安心读书。“这个家,需要人守着。”我顿了顿,迎上他剧烈波动的目光。
一字一句地说。“我不走。”说罢,我又抚着怀里哭个不停地砚欢,轻声安抚。“砚欢乖,
嫂嫂不走。“嫂嫂一直陪着你,嫂嫂还要看着你出嫁呢。”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,
谢二郎紧绷的身体,似乎放松了下来。5谢大郎的抚恤金并没有多少。
给谢母捡几副补药也就没剩什么了。我看着夜夜挑灯夜读的谢二郎,
想起之前在河边听到的话。“谢家二郎是真出息,听说在书院里**考头名。”“可惜了,
这样的好苗子,家里要供不起喽。”“他大哥这一走,怕是真的......。
”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平常百姓家,出一个读书的好苗子不容易。谢家的指望,
婆母的寄托,都在他身上,绝不能耽误了。我得想办法,让他把书读下去。
我告诉谢母想去镇上找个活计。谢母却将我唤到跟前,打开了床头锁着的樟木箱子。
里头不是金银,而是一整套微缩的缂丝工具。细如牛针的梭子,比发丝还细的彩线,
在昏暗中泛着幽光。“这是谢家祖上传下的寸金缂,一幅小像要耗上数月。
”谢母枯瘦的手抚过丝线,眼神悠远。“如今江州城里,识得这手艺的人不少,
也愿意出钱买。“只是,这活极伤眼睛。”这是谢家压箱底的生计。
我毫不犹豫地接过了那些细如发丝的彩线。“娘,我学。”从此,我夜夜守在灯下。
寸金缂很是讲究,手指需在细如发丝的经线间来回穿梭。力道稍有不均,画面便失了神韵。
起初,指尖被锋利的梭子划得满是血口。细密的丝线常纠缠成团,熬到三更天是常事。
抬头时,脖颈僵硬,眼前尽是飞花。但当我将第一幅完成的小像换成银钱时,
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我将换来的银钱仔细分成三份。一份拿去割了半斤猪肉,买了一条鱼。
那晚的饭桌上,久违地飘起了油荤香气。谢母看着碗里我夹给她的鱼肉,眼眶微红。
砚欢更是吃得满嘴油光,小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。另一份,我补了些家用,
又特意为砚欢挑了几本启蒙的浅显读物。小丫头的眼睛亮得像星星。“嫂嫂,
我真的也能像二哥一样读书认字吗?”我摸摸她的头。“当然,我们谢家的姑娘,
也要知书达理。”最后那份,我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,攒着给二郎参加乡试。6春去秋来,
寒暑交替。院中的老梅树又开了新花,转眼便是三年。装着银钱的匣子渐渐有了分量。
而我的眼睛在长年累月的灯下劳作中,也开始畏光、酸涩,视物偶尔会模糊片刻。
我悄悄用冷水敷着,从不在人前显露。乡试之期将近。我翻出早就为谢二郎准备好的行装。
两件新裁的细棉布长衫,针脚密实,穿着舒适。一双厚底千层布的鞋,能耐得住长途跋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