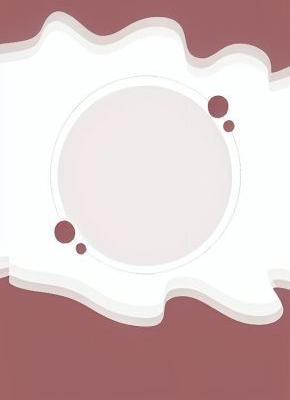《我哥死了十年,他房间的钥匙却在我手里》这本小说章节很吸引眼球,让人看了爱不释手,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,故事之中的主角沈柏行周正沈辉,曲折传奇的故事真的很耐人寻味,看了很多小说,这是最好的!小说精选:桌上有一本摊开的书,旁边放着一支钢笔,笔帽都没盖。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,马上就会回来。我走过去,拿起那本书。是一本《百年……
《我哥死了十年,他房间的钥匙却在我手里》精选:
大寿之日,我亲手将大哥的牌位,放在了祖宗祠堂最不起眼的一角。“沈聿,你这是做什么!
”二叔怒不可遏,指着我的鼻子。我那个高高在上的爷爷,只是冷冷地看着。“让死去的人,
回家而已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可我知道,大哥沈舟,根本就没死。他只是,回不来了。
1沈家老宅的空气,十年如一日的沉闷。檀香和腐朽木料的气味混在一起,
像是棺材里透出的味道。今天是爷爷沈振山七十大寿。我,沈聿,沈家名义上的长孙,
时隔十年,再次踏入这座牢笼。大厅里宾客满座,觥筹交错,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得体的假笑。
我一眼就看到了主位上的爷爷。他穿着一身暗红色唐装,精神矍铄,眼神却像鹰一样锐利,
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时,没有半分温情,只有审视。“阿聿回来了,
过来,坐爷爷身边。”他的声音不大,却瞬间让整个大厅安静下来。我穿过人群,
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二叔沈柏行坐在爷爷下手,皮笑肉不-地扯了扯嘴角。
他旁边的堂弟沈辉,则毫不掩饰眼中的挑衅。“大哥真是稀客,还以为你忘了回家的路。
”沈辉阴阳怪气地开口。我没理他,在爷爷身边的空位坐下。“在外面野惯了,
也该收收心了。”爷爷端起酒杯,“今天大家都在,我只说一句,沈家,一荣俱荣,
一损俱损。过去的事,就让它过去。”他的话意有所指。我垂下眼帘,看着杯中晃动的酒液。
过去的事?哪一件?是大哥沈舟十年前“意外”身亡,还是我因此被送出国外?我母亲,
坐在另一桌,听到“过去的事”四个字时,端着酒杯的手猛地一抖。红色的酒液洒在桌布上,
像一滩刺目的血。她的脸色瞬间惨白。没人注意到这个细节。除了我。宴席冗长而乏味,
像一场精致的木偶戏。结束后,我没有回给我安排的客房。我走向老宅深处,
那个属于大哥沈舟的院子。院门上,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锁。这里被封存了。十年了。
沈辉跟了上来,堵在我身后。“你想干什么?这里是禁地,爷爷不许任何人靠近。
”“我哥的房间,我为什么不能进?”我回头看他。“你哥?”沈辉冷笑一声,
“一个给家族带来灾祸的罪人,你还有脸提他?”“灾祸?”我抓住这两个字。
沈辉的脸色微微一变,随即恶狠狠地说道:“总之,你别想进去,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!
”我没再和他纠缠。回到自己的房间,一切都是崭新的,陌生的。我拉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,
里面空空如也。不对。我伸手到抽屉最内侧的挡板后面摸索。指尖触到一个坚硬冰冷的物体。
是一把小小的,造型古朴的黄铜钥匙。这是我和大哥之间的秘密。当年,
我们用它来藏自己的“宝藏”。我握紧钥匙,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
我再次走向那个被尘封的院子。夜深人静,老宅里只有巡夜下人的脚步声。我避开他们,
悄无声息地来到那扇门前。沈辉已经不在了。我将那把小小的黄铜钥匙,
缓缓**锈蚀的锁孔里。尺寸,完全吻合。轻轻一拧。“咔哒。”一声轻响,在死寂的夜里,
如同惊雷。锁,开了。2推开门的瞬间,一股浓重的灰尘气息扑面而来。
房间里的一切都蒙着厚厚的白灰,像被时光遗忘了。陈设还是十年前的模样。书桌,衣柜,
还有墙上那张已经泛黄的篮球明星海报。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琥珀,
将大哥沈舟离开前的最后一刻,完整地封存了起来。我的目光落在书桌上。
桌上有一本摊开的书,旁边放着一支钢笔,笔帽都没盖。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,
马上就会回来。我走过去,拿起那本书。是一本《百年孤独》。书页里夹着一张书签,
上面是大哥清秀的字迹:“生命中真正重要的,不是你遭遇了什么,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,
又是如何铭记的。”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了一下。我拉开书桌的抽屉。
第一个抽屉是空的。第二个抽屉也空了。第三个抽屉上了锁。又是锁。这个家,
到底有多少秘密需要用锁来守护?我没有钥匙。我看了看四周,
拿起桌上一个沉重的铜质笔筒,对准锁芯的位置,狠狠砸了下去。“砰!
”巨大的声响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。我顾不上那么多,又砸了一下。抽屉裂开一道缝。
我伸手进去,用力一掰。“哗啦。”整个抽屉面板被我扯了下来。里面没有日记,没有信件。
只有一本黑色的硬壳账本。我翻开账本。里面记录的不是正常的生意往来。
一串串陌生的名字,后面跟着日期、货物名称和一长串数字。“过山鲫,三批,二十万。
”“下山虎,一批,五十万。”这些代号一样的词语让我一头雾水。但有一个名字,
出现的频率极高。“老鬼。”每一次“老鬼”出现,后面跟着的数字都格外巨大。
这绝不是我们沈家明面上丝绸生意的账目。大哥在失踪前,到底在做什么?
我正想把账本藏进怀里,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“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。”是沈辉。
他倚在门框上,抱着双臂,脸上满是讥讽。“在这里鬼鬼祟祟地翻什么呢?
想找你那个好哥哥留下的遗物?”我迅速合上账本,把它塞进抽屉深处,然后站起身,
挡住他的视线。“与你无关。”“与我无关?”沈辉笑了起来,“沈聿,我劝你别再查了。
你哥哥碰了不该碰的东西,他那是自寻死路!你如果聪明点,就该夹着尾巴做人,
别步他的后尘。”他的话里,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。“他碰了什么?”我逼近一步,
盯着他的眼睛。沈辉被我的气势逼得后退了半步,随即恼羞成怒。“你没资格知道!
滚出这个房间!”我没有动。我的视线越过他,看到了书桌角落的一个小东西。
那是一个银色的袖扣,造型很别致,是一只展翅的雄鹰。是我送给大哥的十八岁生日礼物。
世界上仅此一对。我趁沈辉不注意,迅速走过去,将那枚袖扣攥在手心。
冰冷的金属硌着我的掌心。“我说了,滚出去!”沈辉见我不理他,彻底被激怒了,
上前来推我。我没再停留,转身离开房间。经过他身边时,我冷冷地说:“我会查清楚的。
”走出院子,回到主路上。夜风吹在脸上,带着一丝凉意。
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院子。就在这时,我看见庭院的角落里,一道黑影一闪而过。
是老管家,权叔。他一直跟在爷爷身边,是沈家的老人了。他正死死地盯着我,或者说,
是盯着我刚离开的那个院子。他的眼神里,不是好奇,也不是监视。
而是一种……极度的恐惧。他发现我在看他,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,慌乱地转过身,
快步消失在黑暗中。我的心,沉了下去。3第二天,我没有声张。那本黑色的账本,
我没能带出来。沈辉的出现,让我意识到,这间屋子,乃至整个沈家,都布满了眼睛。
我唯一拿到的线索,就是那枚鹰形袖扣,以及账本上反复出现的三个字。老鬼。
吃早饭的时候,一家人都在。气氛比昨晚的寿宴更加压抑。爷爷坐在主位,
一言不发地喝着粥。二叔沈柏行不停地用眼角余光瞟我。沈辉则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只有我母亲,担忧地看着我,欲言又止。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,夹了一筷子点心,
随口问道:“妈,我记得以前我们家的丝绸生意,是不是有个外号叫‘老鬼’的合作伙伴?
”“咳!咳咳!”我话音刚落,正在喝茶的二叔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,茶水都呛了出来。
爷爷拿筷子的手也顿了一下。母亲的脸色“唰”地一下变得惨白。她惊恐地看了我一眼,
又飞快地看了一眼爷爷,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“食不言寝不语,
这点规矩都忘了吗?”爷爷放下筷子,声音冰冷。整个饭厅,落针可闻。这一家的反应,
太不正常了。“老鬼”,绝对是关键。吃完饭,我借口出去走走,离开了沈家大宅。
我没有去别的地方,而是打车去了城南的旧货市场。十年前,
这里是本市最繁华的丝绸交易中心。如今,高楼拔地而起,只剩下几条破败的老街,
还残留着当年的影子。我走进一家看起来最古老的绸缎庄。店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,
正戴着老花镜,慢悠悠地用算盘算账。“老师傅,跟您打听个人。”我递上一根烟。
老头抬起眼皮看了我一下,“不抽烟。”“我想问问,十多年前,做丝绸生意的,
有没有一个叫‘老鬼’的?”老头的眼神瞬间变得警惕起来。他放下算盘,摆了摆手,
“没听说过,不知道,你走吧。”一连问了好几家,都是同样的结果。一提到“老鬼”,
所有人都讳莫如深,像是在躲避瘟疫。直到我走进最后一条巷子的尽头。
那是一家快要倒闭的布料店,老板是个瘸腿的中年人。我没有直接问,
而是先买了他店里最贵的一匹布。然后,我将一沓厚厚的钞票压在布料下面。“师傅,
交个朋友。”瘸腿老板看着那沓钱,眼睛亮了。他不动声色地把钱收进口袋,
然后压低了声音。“你问‘老鬼’做什么?那玩意儿可不是人。”“不是人?”我心中一动。
“‘老鬼’,是当年跑江运的一条船的名字。”老板的声音更低了,“专门走夜路,不点灯,
来无影去无踪,跟鬼船一样,所以道上的人都叫它‘老鬼’。”“走江运?运什么?
”“还能运什么?”老板撇了撇嘴,“明面上是丝绸,背地里,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东西。
走私,懂吗?”走私!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那本账本,是走私账!大哥沈舟,
参与了走私?“那条船……现在还在吗?”我追问道。“早没了。”老板摇了摇头,
“十年前,出事了。在一个雷雨夜,船翻了,沉到江底去了,船上的人一个都没活下来。
”十年前。雷雨夜。时间点,完全对上了。“是哪条江?”“就城外那条乌龙江。
”我谢过老板,转身就走。心里乱成一团麻。大哥的失踪,
和这条叫“老鬼”的走私船脱不了干系。他是不是就在那条船上?他是自愿的,还是被迫的?
无数个疑问在我脑中盘旋。我心事重重地回到沈家大宅。天色已经黑了。
我推开自己房间的门。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升起。我的房间,被人翻过了。
衣服被扔得满地都是,床垫被掀开,书桌的抽屉全被拉了出来,里面的东西倒了一地。
他们是在找东西。在找我从大哥房间里拿走的东西。可我只拿了一枚袖扣。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不对。他们找的不是袖扣。我冲到大哥的房间。门没锁。我冲到书桌前,
拉开那个被我砸坏的抽屉。里面空空如也。那本黑色的账本,不见了。4是谁拿走了账本?
沈辉?二叔?还是爷爷?整个沈家,谁都有可能。我站在凌乱的房间中央,
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烧起。他们不仅想掩盖真相,还想抹去大哥存在过的最后痕迹。
我没有去质问,那只会打草惊蛇。我冷静下来,关上房门,开始仔细检查自己被翻乱的房间。
他们翻得很仔细,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但他们没有找到那枚袖扣。
因为我一直把它贴身放在衬衣的口袋里。我坐在床边,将那枚冰冷的袖扣放在掌心。
雄鹰的翅膀,在灯光下闪着冷硬的光。这枚袖扣,是现在唯一的物证了。“咚咚咚。
”房门被敲响。我收起袖扣,起身开门。门口站着的,是二叔沈柏行。他穿着一身真丝睡袍,
手里端着一杯红酒,脸上带着一种虚伪的关切。“阿聿,听说你房间进贼了?
没丢什么贵重东西吧?”我看着他,没有说话。“你看我,真是老糊涂了。
”他自顾自地走进房间,目光扫过一地狼藉,“这宅子老了,安保是不太行。
我已经跟下人说过了,让他们加强巡逻。”他走到我面前,拍了拍我的肩膀。“阿聿啊,
我知道你心里对你大哥的事有疙瘩。但是,人死不能复生,活着的人,总要向前看。
”他的手很用力,像铁钳一样捏着我的肩膀。“有些事,过去了就让它过去。刨根问底,
对谁都没有好处。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,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“你大哥当年,
就是太年轻,太冲动,不懂得审时度势,才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”我抬起头,直视他的眼睛。
“什么绝路?”沈柏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他松开手,抿了一口红酒,眼神变得阴冷。
“一条能毁掉整个沈家的路。”他放下酒杯,凑到我耳边。“他不是在走私丝绸那么简单。
他碰了比那脏一百倍的东西,得罪了我们所有人都得罪不起的人。”“那场船难,不是意外。
”“那是为了堵住他的嘴,为了保全沈家,不得不做的清理。”我的血液,瞬间凝固了。
清理。他用了“清理”这个词。“你最好安分一点,别再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。
”二叔直起身,重新恢复了那副道貌岸岸的样子。“想想你母亲。她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,
你也不想她再为你担惊受怕,白发人送黑发人吧?”这是**裸的威胁。用我最在乎的人。
我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,双拳在身侧死死攥紧。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,传来一阵刺痛。
二叔的话,像一把刀,剖开了真相血淋淋的一角。大哥的死,是人为的。是沈家,或者说,
是二叔,为了自保,牺牲了他。爷爷呢?爷爷在这场“清理”中,扮演了什么角色?是默许,
还是主谋?一股巨大的悲凉和愤怒,像海啸一样将我淹没。我一直以为,这个家虽然冷漠,
但血脉亲情还在。现在我才明白,在利益和秘密面前,亲情一文不值。我走到窗边,
推开窗户。冰冷的夜风灌了进来,让我混乱的大脑清醒了几分。我不能冲动。二叔的警告,
反而让我更加确定,大哥的死背后,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我必须冷静,
必须找到更有力的证据。就在这时,我的目光无意中扫过楼下的庭院。一道瘦弱的身影,
正站在海棠树下,抬头望着我的窗口。是母亲。她不知道站了多久,夜色模糊了她的脸,
但我能感觉到她那道充满哀伤和恐惧的视线。我的心,像被针扎一样疼。她一定知道什么。
她一定知道。我转身,快步走出房间,向楼下跑去。当我跑到庭院时,母亲已经不在了。
只剩下满树的海棠花,在夜风中簌簌发抖,像在无声地哭泣。我站在树下,浑身冰冷。愤怒,
不甘,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。我抬头看着沈家大宅这栋巨大的、黑沉沉的建筑。
它像一只蛰伏的巨兽,吞噬了我的兄长,现在,又想来吞噬我。我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,
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。不是因为害怕。是愤怒。一种想要将眼前这一切虚伪和肮脏,
全都撕碎的愤怒。5我找到了母亲。她在自己的小佛堂里,跪在蒲团上,捻着佛珠,
嘴里念念有词。满室的檀香,也掩盖不住她身上的悲伤气息。我没有出声,
只是静静地站在她身后。不知过了多久,她停了下来,转过身。看到我,她的眼神闪躲,
不敢与我对视。“阿聿,你怎么来了?这么晚了,快去休息吧。”“妈。”我没有动,
声音有些沙哑,“您是不是有话对我说?”她的身体一僵,
手中的佛珠串“啪”的一声掉在地上,珠子散落一地。“我……我没什么好说的。
”她慌乱地去捡。我蹲下身,帮她一起捡。昏暗的灯光下,
我看到了她手腕上那道浅浅的疤痕。是十年前,大哥出事后,她割腕留下的。“妈,
二叔刚才来找我了。”我一边捡珠子,一边平静地说道。她的动作停住了。“他威胁我,
让我不要再查大哥的事。”“他还说,大哥的死,是为了保全沈家。”我抬起头,看着她。
“他说的是真的吗?”母亲的眼泪,像断了线的珠子,滚滚而下。她捂着嘴,拼命摇头,
发出呜咽的哭声。压抑了十年的痛苦,在这一刻,彻底决堤。我没有再逼问她,只是走过去,
从背后轻轻抱住她瘦弱的肩膀。“妈,别怕,有我。”我的声音很轻,
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她在我怀里,哭了很久很久。直到哭声渐歇,
她才抬起布满泪痕的脸,拉着我坐下。“阿聿,听妈的话,我们走吧,离开这里,
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”她的声音颤抖着,“这个家,早就烂透了。”“走之前,
您要告诉我真相。”我坚持道,“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?”母亲闭上眼,脸上是无尽的痛苦。
“你二叔他……他骗了你。”“你大哥他,根本不想参与那些肮脏的勾当。
他发现你二叔利用家里的船运生意走私,一直在偷偷搜集证据,想要去揭发他。
”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原来,大哥不是同流合污,而是在孤身对抗。“他出事那天晚上,
来找过我。”母亲的声音像在飘,“他说他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证据,
要去交给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”“他说,他要去把家里这颗最大的毒瘤挖掉,
让沈家回到正轨上。”“他还说,等事情解决了,就带我和你一起离开这里。
”“我当时好害怕,求他不要去,可他不听……他把这个给了我,让我等他回来。
”母亲从佛龛的一个暗格里,拿出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的小东西。她颤抖着手,打开手帕。
里面,是一张陈旧的火车票票根。是去邻省的火车票。日期,是大哥失踪后的第二天。
他原本计划,把证据交出去之后,就立刻远走高飞。“他走得太急,
把这个落下了……”母亲泣不成声。我接过那张轻飘飘的票根,却觉得它有千斤重。
这是大哥未来得及实现的逃亡计划。我把票根翻过来。在票根的背面,有一行用铅笔写的,
几乎快要磨灭的字迹。是一个地址。字迹很潦草,看得出写的时候非常匆忙。“永安巷,
13号。”没有城市,没有区号,只有一个巷名和门牌号。永安巷,13号。
这就是大哥当晚要去见的人的地址吗?那个他“可以信任的人”,是谁?我正想问母亲,
这个地址是哪个城市的。突然,我手里的票根,被另一只手抽走了。是爷爷。
他不知什么时候,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佛堂门口。他手里拄着那根龙头拐杖,
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。“孽障!”他扬起拐杖,狠狠地朝我砸了过来。我下意识地一躲。
拐杖重重地砸在旁边的木质供桌上,发出一声巨响。“谁让你查的!谁给你的胆子!
”他怒吼着,像一头暴怒的狮子。母亲吓得跪倒在地,拉着他的衣角,“爸,您别怪阿聿,
都是我的错,您要罚就罚我吧!”爷爷一脚踢开她。他走到我面前,
那双浑浊又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“沈舟的死,是为沈家赎罪!你现在要把这个家,
也拖进地狱吗?”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。“我告诉你,沈聿,从今天起,你哪儿也不许去!
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,直到你忘了这些不该记起的事!”他的力气大得惊人,
我的呼吸瞬间变得困难。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,我的指尖,触到了口袋里那枚冰冷的袖扣。
我用尽全身力气,挣脱他的钳制,从口袋里掏出那枚袖扣,举到他面前。“赎罪?
”我喘着粗气,冷笑道,“如果大哥是在赎罪,那这个,又是什么?
”爷爷看到那枚袖扣的瞬间,瞳孔猛地一缩。他脸上的愤怒,在刹那间褪去,取而代之的,
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,混杂着震惊、悔恨和恐惧的复杂神情。他伸出手,想要去碰那枚袖扣,
手却在半空中剧烈地颤抖。“这……这东西,怎么会在你这里?”他的声音,
第一次带上了颤音。6爷爷的反应,比二叔的威胁和母亲的眼泪,更让我确信,
这枚袖扣背后,藏着更深的秘密。他盯着袖扣,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。“说!
这东西你是从哪里找到的!”他失态地抓住我的手腕,力道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。
“在大哥的房间里。”我忍着痛,一字一句地说道。“不可能……不可能……”他喃喃自语,
松开我,踉跄着后退了两步,靠在门框上才站稳。他的脸色,比死人还要难看。
“把……把它给我。”他向我伸出手,眼神里是命令,又带着一丝乞求。我没有动。
“您在怕什么?”我问。“你懂什么!”他突然暴喝一声,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态,
“这是不祥之物!会给沈家带来灾祸!”又是灾祸。所有人都说大哥带来了灾祸。
可没人告诉我,到底是什么灾祸。“爸,您就告诉阿聿吧!”母亲跪在地上,哭着哀求,
“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,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!”“闭嘴!”爷爷怒视着母亲,
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!如果不是你教出那样的好儿子,沈家何至于此!”他将所有的怨气,
都发泄在了我母亲身上。我将袖扣收回口袋,挡在母亲身前。“够了。”我的声音不大,
却让爷爷的咒骂停了下来。“您不敢说,我去查。”“您锁得住门,锁得住人,
但您锁不住真相。”说完,我不再看他,扶起地上的母亲,离开了佛堂。回到房间,
我立刻锁上门。爷爷的失态,让我意识到,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永安巷13号。
我拿出手机,开始搜索这个地址。邻省的省会城市,正好有一条老街,叫永安巷。
就是那里了。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个背包,只带了现金、证件和那枚袖扣。我不能从大门走。
爷爷肯定已经派人守住了。我走到窗边,看了看楼下。二楼的高度,下面是松软的草坪。
我深吸一口气,翻身跃出窗户。落地时,脚踝传来一阵轻微的扭伤,但我顾不上了。
我像一个真正的贼一样,借着夜色和建筑的阴影,避开巡夜的下人,
悄无声息地溜出了沈家大宅。站在大宅门外回头望去,